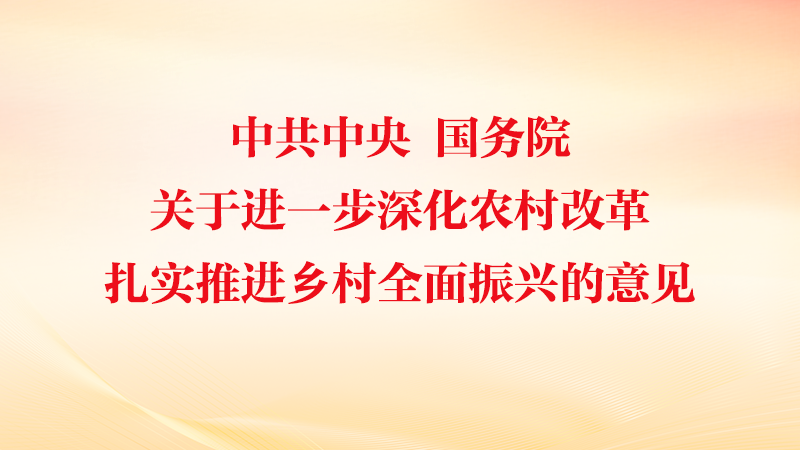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總書記強調創作“有道德”的文藝作品,既是有感而發、針砭時弊,又重申了文藝工作者應當遵循的一條重要準則,即“文藝創作應有‘道德底線’”。
“有道德”,就是教人崇德向善。文藝創作應不應該講道德?這個本不應該成為問題的問題,如今卻成為了文藝界的一大問題。
有的文藝作品崇尚“色情”。從“一夜情”到“一夜性”,從“乳”到“床”,從“喊”到“尖叫”,從畸戀到亂倫,甚至發展成了“下半身寫作”。
有的文藝作品追求“暴力”。一些文藝作品把血腥、兇殺、暴虐等暴力場景寫得細致入微,讓屠殺成為藝術、凌遲成為表演。比如,莫言用整整20頁鉅細靡遺地展示孫丙五百刀凌遲錢雄飛的嗜血場面,叫人毛骨悚然。
之所以出現以上“文藝突破道德底線”的現象,主要原因在于,一些文藝工作者受時下所謂“純藝術”、“純文學”觀念的影響,認為追循道德會束縛創作自由、妨礙藝術想象,從而以維護文藝的獨立性、純粹性為名,提出文藝創作“去道德化”、“為藝術而藝術、為文學而文學”。
文藝作品在道德體系構建中,承擔著重要職能。文藝作品在生動感性的形式中揚善懲惡、寓教于樂,比那些抽象、理性以至教條化的道德勸誡與理論說教更易于為讀者和觀眾所接受,更易于收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效果。
為此,我國古代思想家早就提出文與道、藝與德的關系。早在先秦時代,《左氏春秋》里就提出了“文物昭德”、“樂以安德”的文藝主張,孔子更是把“文質統一”、“盡善盡美”作為最高藝術準則。在中國文藝史上,從《詩經》、《楚辭》開始,歷代優秀的文藝作品,無不以其對現實生活的道德介入潤澤心靈。
在西方,即使是那些主張“純藝術”、“純文學”的人,最終還是把文藝與道德聯系起來。比如,“純藝術”主張的鼻祖康德,認為“美是道德的象征”。那位“為藝術為藝術”觀點的堅定支持者、法國作家泰奧菲勒·戈蒂埃也承認“荷馬的詩、拉斐爾的畫,在提升人的靈魂方面,比一切道德家們的論文所起的作用還要大”。
文藝作品是培育民族精神、引領道德風尚的火炬。一部優秀的文藝作品,會對人的一生產生積極的影響。《鋼鐵是怎么煉成的》、《牛虻》、《紅巖》等文學名著激勵了多少革命青年?而也有一些人,尤其是青少年,在有害讀物的侵蝕下失足成恨,這類例子不勝枚舉。
文藝工作者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期待廣大文藝工作者自覺弘揚文以載道、崇德尚藝的文化傳統,“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創作更多“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記錄精神的跋涉、煥發人性的光輝、引導道德的風尚,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常文)
- 【 2014-10-17 】· 文藝要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樹立正確方向
- 【 2014-10-17 】· 市場不是文藝創作指揮棒
- 【 2014-10-17 】· 文藝創作:人民是活水源頭
- 【 2014-10-17 】· 文藝接“地氣”方能有“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