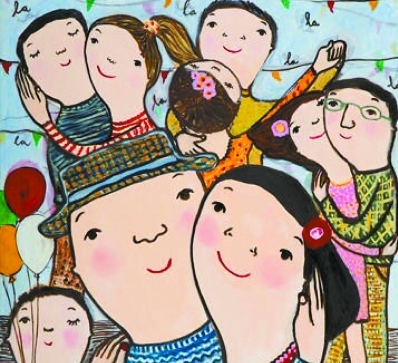蔡文悠希望通過新書與不同年齡層的讀者分享自己的經(jīng)歷,并對(duì)他們有所幫助。 期待藝術(shù)不高冷而能夠分享 從兒時(shí)夢(mèng)想成為甜點(diǎn)師,到八歲那年期待成為一名服裝設(shè)計(jì)師,再到大學(xué)時(shí)放棄服裝設(shè)計(jì)專業(yè)轉(zhuǎn)讀雕塑專業(yè),并在畢業(yè)后繼續(xù)進(jìn)修創(chuàng)意文化產(chǎn)業(yè)課題,在蔡文悠看來,無論怎么“折騰”,自己從小到大的夢(mèng)想似乎總是無法從藝術(shù)中抽離。 對(duì)于從小接觸的藝術(shù),蔡文悠說自己最初是排斥的,問及為何會(huì)選擇學(xué)習(xí)藝術(shù),她坦言,選擇藝術(shù)學(xué)院并不是想要學(xué)習(xí)藝術(shù)或是成為藝術(shù)家,而是出于一種強(qiáng)烈的本能,正如兒時(shí)置身于美術(shù)館中的困惑一樣,她迫切想要了解自己成長的環(huán)境,“正如我想知道為何蒙娜麗莎能吸引世界各地的觀者去一睹芳容”。 “直到進(jìn)了美術(shù)學(xué)院,我才發(fā)現(xiàn),原來做藝術(shù)是一個(gè)很難的過程。” 蔡文悠說,雖然從八歲開始,她就夢(mèng)想成為像日本著名大師三宅一生那樣的服裝設(shè)計(jì)師,但進(jìn)入美國羅德島設(shè)計(jì)學(xué)院開始學(xué)習(xí)藝術(shù)后,她卻開始陷入迷茫,直到與父親探討后轉(zhuǎn)換專業(yè),才重新又尋找到了一個(gè)努力的方向。“爸爸堅(jiān)持要我學(xué)習(xí)當(dāng)代藝術(shù),因?yàn)楫?dāng)代藝術(shù)廣納各種各樣的觀念和材質(zhì),學(xué)成以后我便可以去做任何想做的事,無論是時(shí)裝,還是電影、設(shè)計(jì),甚至是烘焙。” 雖然聽取了父親的建議,但在蔡文悠看來,在藝術(shù)學(xué)院的四年中,自己是帶著些許的痛苦在繼續(xù)著自己的創(chuàng)作。“個(gè)人創(chuàng)作是一個(gè)艱難的過程,我常覺得自己做的作品不如別人的好,而別人進(jìn)步的速度也比我要快。” 面對(duì)這樣的困惑,蔡文悠一直在試圖尋找著答案,她也曾羨慕周遭對(duì)于藝術(shù)一直抱有“饑餓感”的同學(xué),能夠不斷清晰而堅(jiān)定地為創(chuàng)作揮灑熱情,而看看自己,卻總為不能創(chuàng)作出好作品而感到疲憊。直到后來與父親的深入探討后,蔡文悠才慢慢為自己的迷茫找到了答案,原來曾經(jīng)與父親一起去過很多地方,親眼看過許多大師的作品,當(dāng)中的所見所聞其實(shí)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她的創(chuàng)作與眼光,由此也讓她對(duì)于自己的作品有了更多苛刻的要求。而這一次,父親給予蔡文悠的建議,也是她至今難忘的,那就是“不必把一件事情看得太重,但也不要輕言放棄,要始終明確一個(gè)努力的方向”。 “我雖然不想當(dāng)藝術(shù)家,但不得不承認(rèn),藝術(shù)的確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在蔡文悠看來,雖然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過程很難,但在與自己的作品“保持距離”后,往往會(huì)發(fā)現(xiàn)當(dāng)中潛藏著許多的可能性,而正是出于對(duì)這些可能性的好奇,她在大學(xué)畢業(yè)后選擇前往倫敦學(xué)習(xí)創(chuàng)意文化產(chǎn)業(yè)。在她看來,不同于父親的藝術(shù)作品大多收藏在藝術(shù)館中,她更期待藝術(shù)作品被分享的過程,正如此次將自己多年記錄生活的文字集結(jié)成書分享給讀者。而談及如今自己的下一個(gè)夢(mèng)想,蔡文悠則表示,希望如自己所寫的書一樣成為與人分享想法的媒介,在未來,她也想在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中開拓出一個(gè)平臺(tái),讓更多的人在此交流分享藝術(shù),也讓藝術(shù)不再高冷,而是更加貼近社會(huì)大眾。 |
您所在的位置:文明風(fēng)>
熱點(diǎn)圖片
> 正文
其它熱圖
相關(guān)評(píng)論>>

- 文明委成員單位
- 文明行業(yè)
- 地方文明網(wǎng)站
- 福建新聞網(wǎng)站
福建省政府福建人大網(wǎng)福建省政協(xié)網(wǎng)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福建網(wǎng)信網(wǎng)福建省委編辦福建省直機(jī)關(guān)工會(huì)工委福建省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huì)福建省教育廳福建省公安廳福建省民政廳福建省司法廳福建省財(cái)政廳福建省人力資源和社會(huì)保障廳福建省生態(tài)環(huán)境廳福建省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shè)廳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廳福建省衛(wèi)生健康委員會(huì)福建省廣播電視局福建省體育局福建省總工會(huì)福建共青團(tuán)福建省婦女聯(lián)合會(huì)福建省科學(xué)技術(shù)協(xié)會(huì)福建省社會(huì)科學(xué)界聯(lián)合會(huì)福建文藝網(wǎng)福建省殘疾人聯(lián)合會(huì)福建省關(guān)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huì)
中共福建省委文明辦主辦
東南網(wǎng)承辦
文明風(fēng)網(wǎng) 版權(quán)所有
閩ICP備案號(hào)(閩ICP備05022042號(hào)) 閩新備 20060504號(hào) 廣播電視節(jié)目制作經(jīng)營許可證(閩)字第085號(hào)
東南網(wǎng)承辦
文明風(fēng)網(wǎng) 版權(quán)所有
閩ICP備案號(hào)(閩ICP備05022042號(hào)) 閩新備 20060504號(hào) 廣播電視節(jié)目制作經(jīng)營許可證(閩)字第085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