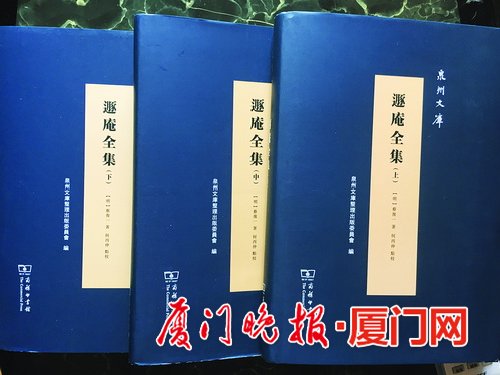
遯庵全集
廈門晚報(bào)訊(記者 龔小莞)近日,明代同安名宦蔡復(fù)一的《遯庵全集》(遯dùn,同“遁”)由商務(wù)印書館出版。廈門市博物館原副館長(zhǎng)、文博研究員何丙仲以山西大學(xué)圖書館珍藏的《遯庵全集》為底本,予以認(rèn)真重新點(diǎn)校。
該書包括《遯庵詩(shī)集》、《遯庵駢語(yǔ)》、《續(xù)駢語(yǔ)》以及《楚牘》、《燕牘》、《鄖牘》、《黔牘》等,同時(shí)將臺(tái)北“中央圖書館”所藏的《遯庵蔡先生文集》手抄本57篇作為附錄。這部書是目前海峽兩岸內(nèi)容最為豐富的一個(gè)點(diǎn)校本。
蔡復(fù)一(1576-1625),福建同安人,晚明時(shí)期閩南富有傳奇色彩的歷史人物。蔡復(fù)一家世貧寒,聰明好學(xué),12歲能寫出萬(wàn)余言的《范蠡傳》,19歲高中進(jìn)士。初任刑部主事,歷任員外郎、兵部車駕、武庫(kù)郎中等京官11年。
蔡復(fù)一“學(xué)博才高,諸著作皆崇論宏議,至?xí)鵂⒆嘧h之文,慷慨談天下事,切中時(shí)弊”。他的詩(shī)作具有明后期竟陵派的特點(diǎn),因而后世評(píng)論明代的詩(shī)文總會(huì)提及他的作品。蔡復(fù)一平生著作甚豐,據(jù)《同安縣志·藝文》所載,計(jì)有《遯庵文集》十八卷,《(遯庵)詩(shī)集》十卷,此外還有《督黔疏草》、《駢語(yǔ)》和《楚愆錄》等。可惜年久月深,大多后世已難獲讀。
點(diǎn)校這部古籍,足足花去何丙仲近3年時(shí)間。滿滿一紙箱的原書復(fù)印件和清樣,他已記不清在千里郵途上往返了多少次。其間何丙仲曾因病住院,他就在病床上進(jìn)行校勘工作。點(diǎn)校過(guò)程中,他發(fā)現(xiàn)作為底本的縮印本邊角上有個(gè)別字模糊不清,廈大的謝泳教授馬上請(qǐng)山西大學(xué)圖書館的朋友幫助辨認(rèn)。
【延伸閱讀】
研究“海絲”文化不可多得的史料
何丙仲說(shuō),《遯庵全集》是研究蔡復(fù)一的重要史料。如:蔡復(fù)一為官始終奉行“三憂三心”的理念,即“憂國(guó)憂民憂身”“報(bào)國(guó)恩以忠心,擔(dān)國(guó)事以實(shí)心,持國(guó)論以平心”,因而他為官廉潔清正。
在湖廣任參政、右布政使時(shí),他曾向上司報(bào)告說(shuō):我父親雖以舉人身份擔(dān)任過(guò)知縣,但家境貧窮,沒(méi)有負(fù)郭之田。“某十六年曹郎,望債家而食,入楚稱貸治裝”,也就是說(shuō)他來(lái)湖北當(dāng)官,路費(fèi)還是借來(lái)的(《楚牘·與兩臺(tái)奏議》)。
蔡復(fù)一的這種言行和思想,在書中比比皆是。
蔡復(fù)一所處的年月,正值閩南月港海商貿(mào)易興盛的大航海時(shí)代。倭患和來(lái)自歐洲的紅夷不斷前來(lái)騷擾。他雖然常年在外,但對(duì)家鄉(xiāng)卻是十分記掛。他在《黔牘中·與南二太撫臺(tái)》這封信中透露出擔(dān)憂:“紅夷疥癬,但與倭合則憂方大。”他嘆息“輪山飲露餐風(fēng),可歌可舞,無(wú)奈紅夷作梗波臣”,向地方官員建議:“夷巨銃難發(fā),發(fā)則銃數(shù)日熱。難再。舟能深而不能淺,人便水而不便陸。兵不敢入攻城,宜靜以待之。”(《鄖牘下·與李任明父母》)類似這些,都是研究“海絲”文化不可多得的史料。
蔡復(fù)一的詩(shī)共十卷,在全集中占有很大比例。詩(shī)集中有不少與詩(shī)友唱酬贈(zèng)答的作品,其中與鐘惺、譚元春等竟陵派詩(shī)人往來(lái)的詩(shī)篇,是研究明后期詩(shī)壇狀況的重要依據(jù)。詩(shī)集中還有類似“磴折寒云行款曲,帆開遠(yuǎn)水見依稀”(《九日輪山》)、“移花未成樹,好鳥已留連。萬(wàn)物各懷新,幽姿聊自妍”(《壺隱山房》)等思念同安故鄉(xiāng)的詩(shī)作。
- 【 2018-08-11 】· 同安愛心驛站:讓高溫下勞動(dòng)者有個(gè)納涼休憩的地方
- 【 2018-08-11 】· 廈門同安龍窟中路一夜被偷了11個(gè)井蓋 竊賊路邊休息被抓
- 【 2018-08-09 】· 同安一中人行天橋已完成多根樁基作業(yè) 預(yù)計(jì)明年初完工
- 【 2018-08-09 】· 同安自閉癥少年走失7天 廈門藍(lán)天救援隊(duì)在山澗找到
- 【 2018-08-06 】· 同安區(qū)恒星義工協(xié)會(huì)成立三周年 選舉產(chǎn)生第二屆理事會(huì)
- 【 2018-08-06 】· 因施工需要 廈門同安區(qū)疾控中等地停水通知
- 【 2018-08-05 】· 穿越古今感受大清盛世 廈門同安影視城演出全新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