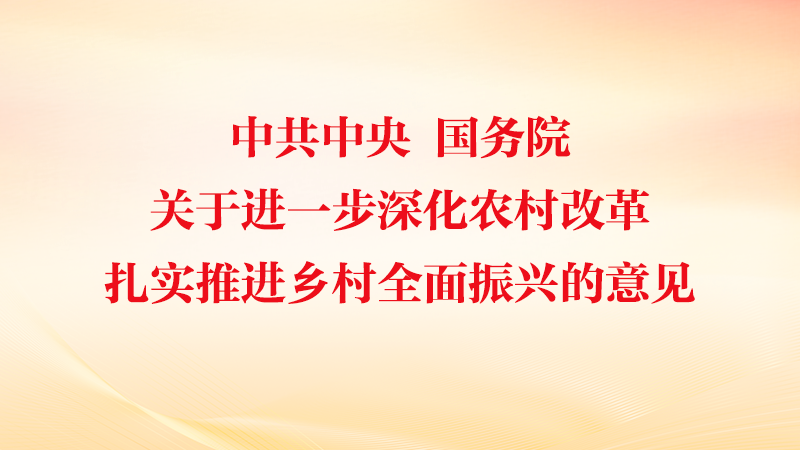福安深山待了一月
“1932年我跟馬立峰去福安一個月,福安地方小,那時還不成根據地,可以搞點小斗爭。當時市委主力放在農村,先搞武裝而后發動群眾。我去福安后,與馬立峰同志首先把不能回家的十幾個同志集中起來,在離福安五六十公里的大山上搞個小隊伍。”1959年10月5日,已是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在《閩東初期革命的斗爭情況》一文中回顧了這段革命生涯。
1931年夏,福建省委派鄧子恢以農村巡視員名義,到閩東開展巡視工作,福安、連江兩地爆發了聲勢浩大的農民“五抗”斗爭。但由于閩東黨組織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也缺乏懂軍事的人,因而公開的武裝斗爭遲遲難以開展,當年的秋收斗爭和翌年的春荒分糧斗爭,均付出了血的代價。尤其是鄧子恢離開后,福安革命更消沉了。于是,時任福安中心縣委書記的馬立峰急忙跑到福州,向陶鑄匯報工作、搬救兵來了。
在點燃連江革命烈火后,陶鑄便騰出手來著重處理福安問題。1932年6月下旬,他一路跋山涉水首赴福安巡視工作。剛在縣委機關一落腳,他就按照事先謀劃,著手布置組織農民暴動和建立工農紅軍的任務。這時,福安縣委已擁有一支秘密游擊隊,但隊員只有陳挺(解放后曾任福建省軍區副司令員等職,少將)等七八人,主要是配合黨組織在福安農村發動群眾性的抗捐斗爭。
陶鑄經過調查了解,吩咐福安縣委在原有秘密游擊隊基礎上,把一批暴露身份不能回家的二三十位黨員和斗爭骨干集中起來,在溪潭馬山村郭厝舉辦黨員骨干訓練班,并介紹了閩西、閩南開展游擊斗爭的經驗。陶鑄根據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階級分析的方法,精辟地分析了閩東地區經濟、政治、軍事、地理位置等方面情況,還幫助閩東黨組織總結了福安平糶斗爭、連江透堡農民減租抗債斗爭得失,批判并糾正黨內在開展武裝斗爭問題上的右傾保守思想傾向,不論從軍事斗爭,還是思想政治上,都讓詹如柏等同志聞所未聞,豁然開朗。
于是,福安縣委決定把整頓游擊隊,開展武裝斗爭作為當地黨組織當前的中心任務,確定了依靠、組織貧苦農民,舉行武裝暴動發展工農游擊武裝作為方向,有力推動了農民運動的發展。農民踴躍報名參加游擊隊,人數很快增加到三四十人。領頭人也有了,陶鑄把這支隊伍的指揮權交給了詹如柏。安排妥這些事,他便返回福州。
陶鑄在福安深山老林風餐露宿待了一個月時間,傳授游擊戰略戰術和軍事斗爭經驗,把游擊隊員訓練成革命戰士,初步改造出了一支懂軍事斗爭策略的隊伍。
據陶鑄撰文回憶:這山村很窮,生活很苦。隊伍就出去打土豪,出去是秘密的,回來也不給人知道,在活動中給當地群眾一點好處,這樣一來一去地活動,我們慢慢站住腳了,地主怕了,我們搞了減租減息,活動逐漸擴大了起來,我離開時,游擊隊就發展幾十人。這樣,福安有了一股,連羅魏耿(后叛變)搞起一股,寧德由葉飛同志搞了一股,壽寧由葉秀藩同志搞了一股,以后曾志同志也去閩東了。這好幾股合了起來,就大發展了。1932年是發展最快的一年,1933年每縣都有一點武裝……
作為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陶鑄需要干的事太多了。因此,他在福安待了一個月,已屬不易。返回福州后,陶鑄仍時時牽掛福安革命工作,并著手物色選派新的巡視員人選。他看到時任共青團福州中心市委書記的葉飛把共青團工作搞得有聲有色,便于1932年8月,派年僅十八歲的葉飛以市委特派員的名義到福安巡視工作。
福安中心縣委的同志根據陶鑄的指示,加緊暴動的準備工作。1932年9月14日中秋前夜,詹如柏、陳挺帶領20多名游擊隊員采取里應外合辦法,化裝襲擊了陳氏地主民團,發動了“蘭田暴動”,繳獲了17支步槍和1支短槍,第二天便正式成立了“閩東工農游擊第一支隊”。分析其戰略戰術,不難看出與“廈門劫獄”手法如出一轍。福州中心市委主辦的《工農報》特地載文《活躍的閩東北工農游擊隊》。
這支隊伍從一開始就具有軍事斗爭經驗和戰斗力,成為閩東紅軍獨立師以及之后改編為新四軍三支隊六團的骨干。葉飛在評價鄧子恢與陶鑄在閩東革命斗爭史上重要作用與貢獻時,有一句精辟的概括:一個是搞農民運動,一個是搞武裝斗爭,這很清楚,歷史就是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