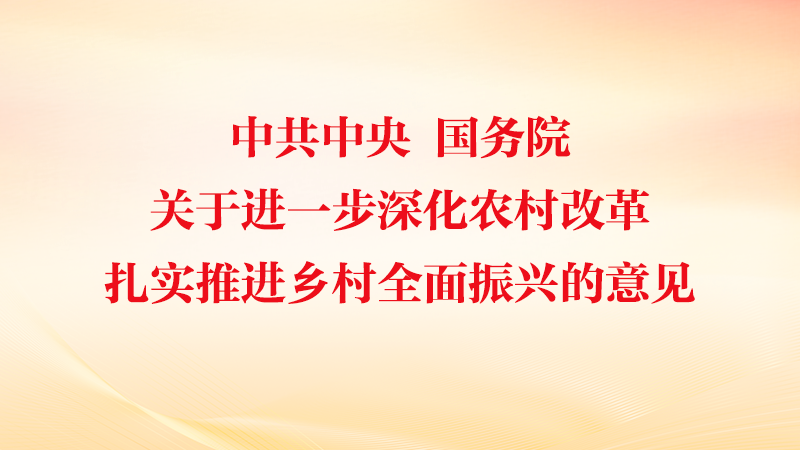東南網(wǎng)8月20日訊(福建日報記者 林祖泉)《莆田史話》(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4年版)是大型歷史知識普及叢書《中國史話》的一個分冊,該書由莆田學(xué)院的教授、研究員、博士等組成編寫班子,并且“編著者除了親自做田野調(diào)查外,參考的古今文獻(xiàn)亦不下百種”(后記)。應(yīng)該說,此書的權(quán)威性和學(xué)術(shù)性是較高的。
然而,筆者拜讀全書后,卻意外發(fā)現(xiàn)書中明顯存在概念不清、史料不明、數(shù)據(jù)不準(zhǔn)等諸多問題,如“宋代福建莆田有沒有特奏名狀元”就是一個例子,故撰文與編者商榷。
狀頭與狀元
此書“宋明科甲傳佳話”一節(jié)中寫道:“莆田古代科甲鼎盛,共出過進(jìn)士2482名,各類狀元21人(包括文狀元9人、武狀元2人、特奏名狀元8人、釋褐狀元2人),還有榜眼7人、探花5人。”這里暫且不談進(jìn)士、榜眼和探花人數(shù)的不準(zhǔn)確,單說狀元人數(shù)的虛高。
眾所周知,“狀元及第”是中國科舉制度中的最高榮譽(yù)。稱進(jìn)士第一人為狀元,始于唐武德五年(622年),亦叫“狀頭”。但由于設(shè)置科目不一,考試內(nèi)容有別,選拔程序不同,唐代的狀元與后世的狀元不盡相同。唐進(jìn)士之選每年舉行一次,地方各州向中央貢送的舉子在應(yīng)試前,先向禮部遞呈州里的解狀及各舉子出身、履歷等親狀,稱為“投狀”。錄取后,禮部又把這些新進(jìn)士的身份材料及成績一起報送皇帝,稱為“奏狀”,排在最前面的即是狀頭。
北宋以后,對科舉制度進(jìn)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尤其是皇帝殿試策問成為定制,科舉形成解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制度,遂稱進(jìn)士解試第一人為“解元”,省試第一人為“省元”,殿試第一人為“狀元”。由此,狀元的聲名、身價、地位一下子高拔許多,更顯出不同一般的意義,故與唐朝的狀頭不可同日而語。
千百年來,狀元作為“學(xué)而優(yōu)則仕”傳統(tǒng)觀念的最高標(biāo)識,受到各朝各代統(tǒng)治者的青睞和旌表,成為士人學(xué)子所憧憬和追逐的目標(biāo),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市井百姓無不仰慕和欽羨。同樣,“大魁天下”也成為宋代福建莆田(時稱興化軍)文人孜孜以求的目標(biāo)。
據(jù)明代朱希召編的《宋歷科狀元錄》載,宋代共產(chǎn)生出118名文狀元,其中有5名籍貫不明。在有籍貫記錄的113名文狀元中,福建籍狀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了5名,即徐鐸、黃公度、鄭僑、吳叔告、陳文龍,占福建狀元的1/4多。毋庸置疑,這已經(jīng)是一份了不起的科考成績單。卻不知《莆田史話》的編者何以還不滿足,非要畫蛇添足,多出“特奏名狀元8人”?
何謂特奏名
其實,在由唐至清朝的歷科進(jìn)士中,唯獨宋代于正奏名進(jìn)士之外,還有特奏名進(jìn)士。
何謂特奏名?《宋史·選舉志》云:“凡士貢于鄉(xiāng)而屢絀于禮部,或廷試所不錄者,積前后舉數(shù),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徑許附試,故曰特奏名。”這就是說,所謂特奏名,就是凡解試合格而省試或殿試落第的舉人,積累到一定的舉數(shù)和年齡,不經(jīng)解試、省試,即由禮部特予奏名,直接參加殿試,分別等第,并賜出身或官銜的一種科舉制度。
宋開寶三年(970年),在禮部錄取了張拱等8位進(jìn)士之后,宋太祖為了牢籠士人,安撫貧寒年老舉子,設(shè)立了特奏名進(jìn)士,將進(jìn)士、諸科十五舉以上且考試終場者106人特賜本科出身,是為宋代特奏名之始。為了申明此舉的意圖,他還下詔說,“漢詔有云:結(jié)童入學(xué),白首空歸。此蓋愍乎耆年無成而推恩于一時也。朕務(wù)于取士,期在得人,歲命有司大開貢部,進(jìn)者俾升上第,退者俟乎再來。而禮闈相繼籍到十五舉已上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皆困頓風(fēng)塵,潦倒場屋。學(xué)固不講,業(yè)亦難專,非以特恩,終成遐棄”(《宋會要輯稿·選舉》)。
特奏名的設(shè)立,使科舉考試更具吸引力,它不僅意味著取士名額的增加與擴(kuò)大,而且也使讀書人應(yīng)舉的前程顯得更加光明。然特奏名的兩個主要條件是“舉數(shù)”和“年甲”而不是才學(xué)高下,所謂“退者俟乎再來”,則為每一個科場失意者始終保留著下一次成功的機(jī)會與希望,而只要存在著這種機(jī)會與希望,一般士子就不會輕易放棄舉業(yè)鋌而走險。
對此,南宋王栐在《燕翼貽謀錄》卷一《進(jìn)士特奏》中有如下一段精彩論述,“唐末進(jìn)士不第,如王仙芝輩倡亂,而敬翔、李振之徒,皆進(jìn)士之不得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廣,而歲上第者僅一二十人,茍非才學(xué)超出倫輩,必自絕意于功名之途,無復(fù)顧籍。故圣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于賊盜奸宄……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死不止。進(jìn)士入官,十倍舊數(shù),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杰,皆淚沒消磨其中,故亂不起于中國而起于夷狄,豈非得御天下之要術(shù)歟”!
可見宋代統(tǒng)治者創(chuàng)立特奏名制度,主要是吸取了唐末王仙芝等人因進(jìn)士不第而犯上作亂的教訓(xùn),特意大量增加取士名額,使潦倒場屋、屢試不中的廣大舉人心存一線希望,通過陪同正式考生參加殿試(即“附試”)的機(jī)會,博取功名,進(jìn)入仕途,不致積憤造反。
特奏名之弊
據(jù)宋朝文獻(xiàn)資料載,北宋前期,一般是曾經(jīng)省試進(jìn)士五舉或六舉、諸科七舉或八舉、年齡在50以上,特予奏名。
北宋中期,一般是曾經(jīng)殿試進(jìn)士三舉、諸科五舉年50以上,曾經(jīng)省試進(jìn)士五舉年50、諸科六舉年60以上,特予奏名。
北宋后期,一般是“進(jìn)士五舉、諸科六舉曾經(jīng)御試下,進(jìn)士六舉、諸科七舉省試下,年50以上;進(jìn)士七舉、諸科八舉曾經(jīng)御試下,進(jìn)士九舉、諸科十舉省試下,年40以上”,特許奏名(《宋會要輯稿·選舉》)。
南宋時期,“進(jìn)士六舉曾經(jīng)御試、八舉曾經(jīng)省試,并年40以上;進(jìn)士四舉曾經(jīng)御試、五舉曾經(jīng)省試,并年50以上”,特許奏名。總之,北宋后期較嚴(yán),而南宋時期稍寬。
凡特奏名者,不論殿試成績?nèi)绾危n予一定的出身或官銜。在太祖、太宗朝,尚未分等第,均賜本科出身。真宗、仁宗朝,一般分為三等,賜本科出身,試將作監(jiān)主簿,諸州長史、文學(xué)、助教。英、神、哲、徽四朝,一般分為五等,第一等賜同本科出身、假承務(wù)郎(登仕郎),第二等京府助教,第三等上州文學(xué),第四等下州文學(xué),第五等諸州助教。
南宋時,仍分為五等,一般第一等第一名賜同進(jìn)士出身,第二、三名賜同學(xué)究出身,第一等第四名以下賜登仕郎,第二等京府助教(將仕郎),第三、四、五等與英、神、哲、徽朝的三、四、五等相同。
作為籠絡(luò)士子的一種手段,特奏名辦法出臺后,在維持宋朝境內(nèi)安定方面發(fā)揮了一定的功能。然特奏名入仕者任官比正奏名進(jìn)士低,多數(shù)是授州府官學(xué)助教一職,這雖有促進(jìn)官辦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的作用,但特奏名制度也使科舉的選賢任能功能變?yōu)檫x賢任能與養(yǎng)士撫庸相輔并行了。據(jù)張希清《論宋代科舉取士之多與冗官問題》(載《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1987年第5期》一文中的統(tǒng)計和推算:“兩宋貢舉共取士109950人,其中特奏名者即達(dá)50352,占45.8%。”可見宋代特奏名進(jìn)士之多。
由于特奏名進(jìn)士是宋王朝對內(nèi)收買人心、防止士人造反,特意大增取士名額的產(chǎn)物,是對多次落榜的舉人進(jìn)行再試由皇帝特恩“各賜本科出身”,它不能代表進(jìn)士的真實水平,所以對于特奏名進(jìn)士的人數(shù),一般不列入由唐至清朝的進(jìn)士總數(shù)中進(jìn)行統(tǒng)計。而且,這些特奏名者大多才學(xué)較低,年事又高,故出官之后,不少人不能持廉奉法,盡心治事,往往迫不及待地貪贓枉法,中飽私囊,以為歸老之計。此外,特奏名制度引誘士人皓首窮經(jīng),老死場屋,對廣大士人本身也是一種殘害。
那么,宋代福建莆田的特奏名進(jìn)士到底有多少人呢?根據(jù)明《八閩通志》《興化府志》等志書統(tǒng)計,從宋元豐五年(1082年)黃裳榜起至咸淳十年 (1274年)王龍澤榜止,192年間共計特奏名進(jìn)士582人。而從宋建隆元年 (960年)楊礪榜起至咸淳十年(1274年)王龍澤榜止,314年間莆田正奏名進(jìn)士只有1014人。
綜上所述,本文的結(jié)論是宋代福建莆田只有特奏名進(jìn)士,而沒有特奏名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