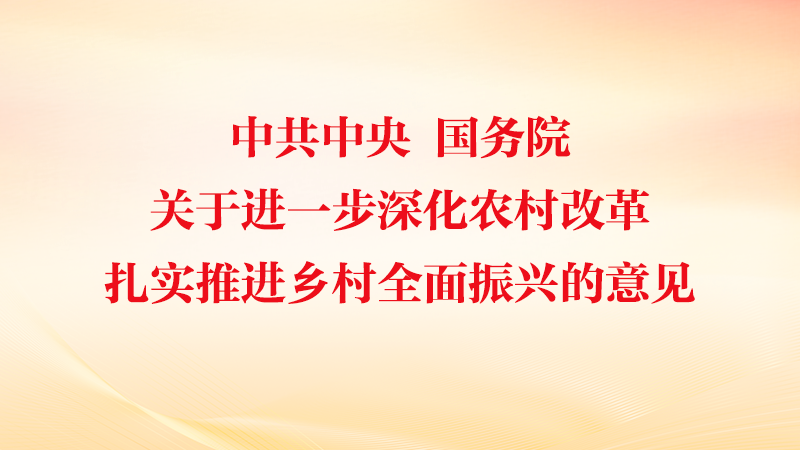東南網(wǎng)8月20日訊(福建日報記者 林祖泉)《莆田史話》(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是大型歷史知識普及叢書《中國史話》的一個分冊,該書由莆田學(xué)院的教授、研究員、博士等組成編寫班子,并且“編著者除了親自做田野調(diào)查外,參考的古今文獻亦不下百種”(后記)。應(yīng)該說,此書的權(quán)威性和學(xué)術(shù)性是較高的。
然而,筆者拜讀全書后,卻意外發(fā)現(xiàn)書中明顯存在概念不清、史料不明、數(shù)據(jù)不準(zhǔn)等諸多問題,如“宋代福建莆田有沒有特奏名狀元”就是一個例子,故撰文與編者商榷。
狀頭與狀元
此書“宋明科甲傳佳話”一節(jié)中寫道:“莆田古代科甲鼎盛,共出過進士2482名,各類狀元21人(包括文狀元9人、武狀元2人、特奏名狀元8人、釋褐狀元2人),還有榜眼7人、探花5人。”這里暫且不談進士、榜眼和探花人數(shù)的不準(zhǔn)確,單說狀元人數(shù)的虛高。
眾所周知,“狀元及第”是中國科舉制度中的最高榮譽。稱進士第一人為狀元,始于唐武德五年(622年),亦叫“狀頭”。但由于設(shè)置科目不一,考試內(nèi)容有別,選拔程序不同,唐代的狀元與后世的狀元不盡相同。唐進士之選每年舉行一次,地方各州向中央貢送的舉子在應(yīng)試前,先向禮部遞呈州里的解狀及各舉子出身、履歷等親狀,稱為“投狀”。錄取后,禮部又把這些新進士的身份材料及成績一起報送皇帝,稱為“奏狀”,排在最前面的即是狀頭。
北宋以后,對科舉制度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尤其是皇帝殿試策問成為定制,科舉形成解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制度,遂稱進士解試第一人為“解元”,省試第一人為“省元”,殿試第一人為“狀元”。由此,狀元的聲名、身價、地位一下子高拔許多,更顯出不同一般的意義,故與唐朝的狀頭不可同日而語。
千百年來,狀元作為“學(xué)而優(yōu)則仕”傳統(tǒng)觀念的最高標(biāo)識,受到各朝各代統(tǒng)治者的青睞和旌表,成為士人學(xué)子所憧憬和追逐的目標(biāo),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市井百姓無不仰慕和欽羨。同樣,“大魁天下”也成為宋代福建莆田(時稱興化軍)文人孜孜以求的目標(biāo)。
據(jù)明代朱希召編的《宋歷科狀元錄》載,宋代共產(chǎn)生出118名文狀元,其中有5名籍貫不明。在有籍貫記錄的113名文狀元中,福建籍狀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了5名,即徐鐸、黃公度、鄭僑、吳叔告、陳文龍,占福建狀元的1/4多。毋庸置疑,這已經(jīng)是一份了不起的科考成績單。卻不知《莆田史話》的編者何以還不滿足,非要畫蛇添足,多出“特奏名狀元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