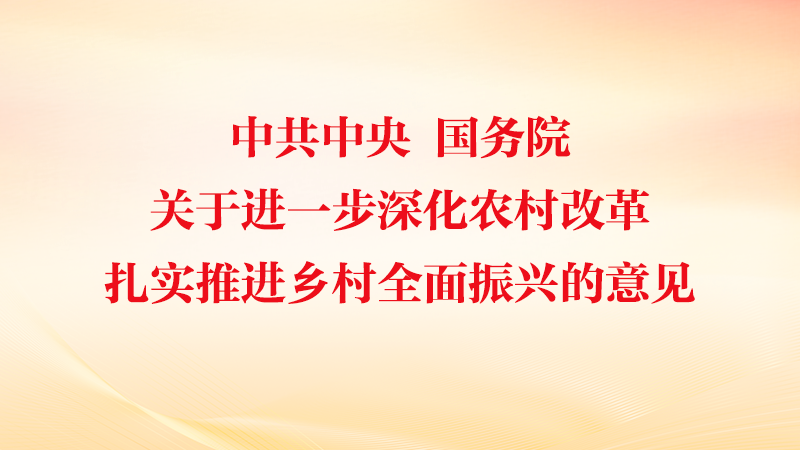東南網7月16日訊(福建日報記者 謝海潮)連環(huán)畫《說岳全傳》之“黃天蕩”,幾成“70后”兒時的集體記憶。然其事實原委播傳人口,難免因走樣變形而近乎傳訛。及長,猶有同事帶著一臉“壞笑”說:在黃天蕩助金兀朮鑿通老鸛河故道遠遁者,為福建一漁翁。
當時亦感納悶:一福建漁翁何以不憚劬勞,遠赴南京附近的內河打魚作甚,居然還不會人地兩疏,當起了“帶路黨”?殊不可解!近來求證于書,愈覺此事大有商榷余地,試為一辨。
黃天蕩“獻謀”
黃天蕩一戰(zhàn),本身就言人人殊,想要勾勒大概的輪廓尚屬不易。所幸楊倩描、周寶珠諸位先生考證甚為精當,且戰(zhàn)事爭議非本文討論主旨,在此只需厘清所謂“閩人”跟此戰(zhàn)有何關聯即可。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冬,金兵分兩路渡過長江。建炎四年(1130年)春,兀朮退兵,由于掠奪財物太多,“以輜重不可遵陸”,只得沿浙西運河北撤,水陸并行,擬由鎮(zhèn)江出運河渡長江北返。事先屯兵鎮(zhèn)江焦山的韓世忠,“以江船鑿沉于閘口,拒金人之出”。
據楊倩描《宋金鎮(zhèn)江“金山大戰(zhàn)”考實》所述,三月十七日夜,金軍船隊趁東北風大起、宋軍麻痹大意,“別開一河出江”。韓世忠發(fā)覺后,率水軍尾隨追擊,迫使金船改道西上前往建康(今南京),從而將之逼入黃天蕩(在今南京東北八十里處)。
記載宋金交戰(zhàn)的文獻中,“黃天蕩”一名初見于《韓蘄王神道碑》(作于1176年)。楊倩描認為,所謂宋金黃天蕩之戰(zhàn),應包含三次戰(zhàn)斗,即鎮(zhèn)江之戰(zhàn)(金山大戰(zhàn))、“黃天蕩之戰(zhàn)”、建康之戰(zhàn)。多數史籍將三戰(zhàn)混記一起,以至時間、地點、戰(zhàn)斗順序混亂不堪,矛盾百出。綜合周寶珠、楊倩描的論文分析,金船出鎮(zhèn)江、黃天蕩、建康,開河至少三處,在此不贅。
無論開河幾處,從較早述及金兵渡江的孫覿《韓世忠墓志銘》、建陽人熊克《中興小紀》,后出的《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乃至現存最早的南京地方志《景定建康志》,其卷十九“山川志三·河港”及卷三十八“武衛(wèi)志一·江防”,但凡涉及金兵鑿渠一事,如“一夕濳鑿小河自建康城外屬之江以通漕渠”等處,哪有“閩”或“福建”的字眼?“漁翁”亦未有見。所謂“福建漁翁”,或是將明清世情小說《金屋夢》中被擄金營的“閩人”“鄉(xiāng)(向)導官”記混了吧?
《三朝北盟會編》再詳盡,也就多了“或獻謀于金人”六字,連“土人”“士人”都不提。獻謀開河的“閩人”,真是“莫須有”三字!
“閩人王某”所出
韓世忠艨艟大艦為海船,金人舟小。《宋史·韓世忠傳》提及兀朮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搖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宋史》入列煌煌二十四史,“閩人王某”獻破海舟策一說似可信服。事當在建康之戰(zhàn)。
然元人“手懶”,所修《宋史》以舊有宋朝國史為底本,參考了徐夢莘等私家撰述,略加編次而成,所以大可跳過,徑直從宋人的原始記錄中溯源。今查“閩人獻策”較早出處,只能找到《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兩部私史。
《要錄》卷三十二云:“有福州人王某僑居建康,教金人于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在此可知,“閩人王某”原系僑居建康的福州人;較之《宋史》,破海舟策還多了火箭火攻一計。
《會編》卷一百三十八則云:“有福州百姓姓王人,僑居建康開米鋪為生,見榜有希賞之心,乃教兀朮于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俟無風則出江,有風則不出。海船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這句近于白話,所說的王姓福州百姓,又比《要錄》細致,具體到“開米鋪為生”的交代;“見榜有希賞之心”,動機也有了,看似“細節(jié)可以創(chuàng)造真實”。
李心傳(1167年—1240年)的《要錄》“博參群書,多所考定”,引用徐夢莘(1126年—1207年)《會編》“共計54次”。元修《宋史》時未見《要錄》,無論從履歷還是文本看,“閩人王某”之說脫胎于徐夢莘之書,大體不差。只是“王某”有姓無名,其個人信息之后未見增益,反倒越發(fā)含糊,這點有悖常情。
《會編》之檢討
鄧廣銘先生認為《會編》“不愧為宋金關系史料之淵藪”,但也說徐夢莘在搜集史料的鑒別和使用上存在某些問題,“有些史料的真實性是很值得懷疑的”。如“粘罕以病殂”一條,“像這樣明顯有問題的材料照說是不應該被采錄的”。
《會編》有關獻破海舟策的文字一段,前有“《(中興)遺史》曰”,后有“《中興姓氏錄·忠義傳》曰”,而此段既無注明出處,且在“二十五日丙申,韓世忠與兀朮再戰(zhàn)于江中,為兀朮所敗。孫世詢、嚴永吉皆戰(zhàn)死”的事目下直接走筆,顯系出自徐夢莘之手的著述。
把“閩人王某”的籍貫、職業(yè)都道明了,卻不具名。若說是行文風格,或因涉事人地位低微、聲名不顯,故不書名,也不盡然。《會編》卷一百十九記載建炎二年(1128年)十一月,“金人寇開德府,王某守其城”,金人佯稱“知府王某有文字來歸附大金”,致使這位知府被自己的軍民蹂踐而死。《宋史》本紀則云:“又陷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顯然,《宋史》的編纂者見過徐夢莘未見的史料,所以直書“王棣”其名,但在“閩人王某”的考校上,卻只好蕭規(guī)曹隨、不出窠臼,似能說明此乃徐夢莘一家之言,且言之已盡,是為孤證,除此無他。“閩人王某”何以至今仍“見事不見人”,也就好理解了。
再就《會編》這兩個“王某”而言,“閩人王某”的個人信息量比“知府王某”略多,說明徐夢莘治史并無尊卑之分,按其自序“悉取銓次”的原則,如有可能,想必也愿意一一贅述,巨細無靡。問題是,有些事徐夢莘的確知之未詳,私人修史畢竟力有不逮。
建炎三年,金兵陷臨江軍,“公之生才四年,母氏襁負走陂頭劉氏家,僅免于難”(《直秘閣徐公墓志銘》)。徐夢莘是臨江(今江西省樟樹市臨江鎮(zhèn))人,可見他幼時躲避的是襲洪州(今南昌),追蹤隆祐太后的另一路金兵,與“犯江浙”無干。獻破海舟策一事,不可能是徐本人及其家人的親歷耳聞,何況當時他才四五歲大。
或謂征之故老。《會編》“收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余家”,引用《中興遺史》次數最多,共140多處。許起山在《中興遺史輯校》前言中說,《遺史》所記宋欽宗、宋高宗朝史實,多是趙甡之的耳聞目睹,可謂當代人寫當代史,“要比徐夢莘、李心傳等人更有優(yōu)勢”。有關對“閩人王某”的嚴重指控,《遺史》等書沒有“拾遺”,宋元兩代南京地方志未錄(特別是元至正《金陵新志》在按中已見《宋史》引文,卻未采“閩人”一說),徐夢莘的獨家爆料搶了頭香,何以在文中只字不提消息來源?“雜博”是《會編》的優(yōu)點,由此也可能帶來某些風聞無據之言。
親歷人的指證
那么,今天還能找到“金人犯江浙”的現場證言嗎?還真有,那就是胡舜申的《己酉避亂錄》。建炎四年三月,胡舜申(徽州績溪人,后遷蘇州)及其兄胡舜陟(南宋官員,《宋史》有傳)拖家?guī)Э冢豁n世忠部將董旼強行帶往焦山避難。
胡舜申無疑更有發(fā)言權。既至焦山,“時虜已破鎮(zhèn)江,日見虜騎馳逐于江岸,坐見其焚甘露寺,但留雙鐵塔。世忠以江船鑿沉于閘口,拒虜人之出,虜船實不可出,以閘口沉船縱橫也”。三月十七日晚,胡舜申獨宿船中守行李,“東北風作,至夜益甚,江中飄水皆成冰”。及曉,“及伸首船外,視焦山之前,唯吾一船而已,余皆不知所在”。
楊倩描綜合史料印證,對這本書披露戰(zhàn)事的真實性、準確性給予肯定。但因書載韓世忠攜妓等事,《四庫全書》館臣說胡舜申“頗詆世忠”“未必實錄”。然而,胡舜申生前從未對外吐露書中的只言片字,《己酉避亂錄》終宋一代未曾面世,楊倩描認為,這恰好說明此書并不是出于詆毀才寫的,而只是為了真實記錄,一發(fā)對南宋初年政治、軍事腐敗的憤慨而已。
胡舜申看了什么,聽了什么,令他如鯁在喉?一大情形是,“始虜在鎮(zhèn)江不可出江,即陸往建康,嘗聚吾宋士大夫,令籌所以破世忠軍,皆云:‘海船如遇風不可當,船大而止,且使風可四面,卒難制,如風使舟耳,卒難搖動。’虜然之。選舟載兵,舟櫓七八乘。天曉,風未動,急搖近世忠軍,以火箭射之,船人救火不暇,又無風,船不可動,遂大敗”。
請注意“吾宋士大夫”“皆云”兩個關鍵詞!兩宋之交,朝野上下多“偷生嗜利之徒”。建康先陷于建炎三年,御營使杜充、戶部尚書李棁、顯謨閣直學士陳邦光,這些駐地最高軍政長官早就率眾降了。金人盤踞半年多,不乏“專業(yè)人才”供其驅使,何必多此一舉,把軍機大計搞得跟唱戲文似的,“揭榜立賞”募來“開米鋪為生”的小百姓,獻個跟“吾宋士大夫”“皆云”幾乎一樣的破法?
退一步說,即便“閩人王某”并非烏有先生,也湊在了“吾宋士大夫”群中揭榜獻策,只是這歷史的共業(yè),又豈能單單坐實到某地一人身上?唯有存真求實,才有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反思。
新出“福州書生”
曾見網上有人問:黃天蕩一戰(zhàn),為什么會有當地漢人幫助金兀朮脫險?
有位網友答:王曾瑜先生的歷史紀實小說有具體情節(jié)。獻計的漢奸叫王知全,是來自福州的落第秀才,自以為在宋“懷才不遇”,便向金人獻計,另開一條新河,直抵建康城西白鷺洲江面,并且按宋軍的戰(zhàn)術,趕造了大批火箭。兀朮帶他回北方,但他在過江時,因得意忘形,被幾個降金的南宋官員推下船淹死。
網友這番孟浪之言,出自王曾瑜《大江風云》“黃天蕩之戰(zhàn)”等章節(jié)。書無注釋,依據何在?但看“王知全”一名,顯為游戲之筆,“知識全面”的書生當“軍師”,上知下知,不然怎能開河、火攻的技術活全給包了。
王曾瑜為著名宋史研究專家,觀其專著《岳飛新傳》不作妄言,何以在冠名“紀實小說”中多有闡發(fā)?不過,他對“閩人王某”的改頭換面,反證了原型人物在可信度上的先天不足,不堪其用。《宋史》不錄“閩人王某”“以火箭射”一策,或已有疑?
徐夢莘順帶一筆,因元朝史官們“不甚措意”而倉促寫定,加之黃天蕩一戰(zhàn)日后被演義化,“閩人王某”竟成某種意義上的歷史代名詞,可對于這個人,誰又能說出個子丑寅卯來。
將傳說、演義、史籍因襲附益,“閩人王某”“閩人鄉(xiāng)導”“福州書生”等角色發(fā)生層累式變換,不知伊于胡底?過去說“文人不能修史”,現在看來,“修史者不作戲文”也應援引成例。
- 【 2018-07-13 】· 廈門湖里:破除陳規(guī)陋習 延展宮廟功能引領文明新風
- 【 2018-07-13 】· 廈門湖里:破除陳規(guī)陋習 延展宮廟功能引領文明新風
- 【 2018-07-13 】· 龍海:提升城市“顏值氣質” 鋪就市民“文明紅利”
- 【 2018-07-13 】· 鯉城開辟移風易俗文化墻 倡樹文明新風
- 【 2018-07-13 】· 永安市“軟硬兼施”抓好爭創(chuàng)全國文明城市工作
- 【 2018-07-13 】· “共享廁所”放大城市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