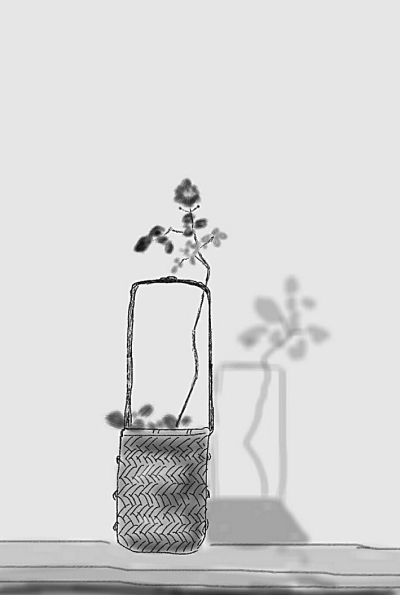
插圖:殷燕召
一
拈出元曲中這個曲牌來做題目,意在探討一個審美的課題。說是賞花,卻著眼于“時”字,取其把握時機、恰當其時之義。
事物發展進程中,可分為準備、進行、完成幾個時段;花的開放,同樣也有含苞待放、初開、盛開等多種狀態。那么,就賞花來說,哪種狀態最受人青睞呢?古人說了,“好花看到半開時”。
從審美的角度說,如果花蕾還緊包在萼片里,挺然直立花叢中,確實也沒有什么好看的;而當花已盛開,東風起處,偶有幾片飄飛,也會讓人聯想到接下來的凋零破敗,從而萌生出盛景不常的蒼涼意緒,尤其是那“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的詩句,著實令人神情蕭索。倒是開了又未全開,既可滿足人們賞花的熱切愿望,又會產生一種“好戲還在后面”的審美期待。花未全開,色、香、味或許尚未達到極致,而其蓄勢待發、有余未盡的潛在魅力,生機勃發的向上活力,則會給賞花人留有想象發揮的空間,可能還會平添一份擔心——牽掛本身就是一種吸引力:過后這些天可不能有疾風驟雨啊!有人說:“最深的愉悅不是得到某樣東西,而是在得到它之前的努力;最漂亮的東西,不是看到它時的表述,而是在看到之前的幻想;最美好的結局,不是那句‘王子和公主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而是對那個未知結局的猜想。”這類微妙而復雜的心理活動,氤氳了審美的情趣,牽動著人們的想象力。
乾隆時期的著名詩人蔣士銓,有一首為清初畫家王石谷所繪玉簪花的題詩:“低叢大葉翠離離,白玉搔頭放幾枝。分付涼風勤約束,不宜開到十分時。”詩句先是狀寫畫中玉簪花的葉子,翠色紛披,鋪排繁茂,然后渲染女子首飾玉搔頭形狀的花蕊。這個玉搔頭,可不同凡響,當年漢武帝的李夫人曾以玉簪搔頭,故而得名;后來又被大詩人白居易寫進《長恨歌》里,“翠翹金雀玉搔頭”。畫面上,大量花蕊含苞待放;而正開的不過寥寥幾枝。應該說,這是玉簪花生機勃發、生命力最旺盛、花容最美麗的時刻。寫到這里,詩人發話了:得趕緊吩咐撲面的涼風,要對玉簪花勤加約束,別讓它急著開下去,以免迅速迎來“花謝花飛花滿天”的慘淡局面。這里“涼風”二字極有分寸,不能是“其色慘淡”“其氣栗冽”“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的蕭颯金風,那樣,玉簪花很快就沒戲了。又要它健壯地生長著,又要它放慢開放的步伐,充分表現了詩人愛美惜花的良苦用心。當年,詩圣杜甫就曾深情無限地吟詠過:“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蕊商量細細開。”(《江畔獨步尋花》)
二
清代詩人查慎行有一首五絕:“無數緋桃蕊,齊開仲月初。人情方最賞,花意已無余。”詩人作為審美主體,對眼前“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這如霞似錦的美的形態,作了直接的形象感知和清醒的理性判斷:“無數緋桃蕊”的“齊開”,造成了“人情方最賞”的轟動效應;而此刻所呈現的恰是“花意已無余”的審美形態。“無余”二字,是對緋桃生氣已經耗盡,美麗轉瞬消失,行將枯萎凋殘的絕好概括。這里反映了事物相反相成的規律。
寥寥二十字,啟發人們思考一些有關盛衰、榮瘁、盈虛、消長的哲學理蘊,也聯想到戒滿忌盈、避免絕對、勿走極端、留有余地這些日常處世原則。
讀過明代短篇小說集《警世通言》的朋友當會記得,在《王安石三難蘇學士》中有這樣一段話:“古人說得好,道是:‘滿招損,謙受益。’俗諺又有‘四不可盡’的話。那(哪)‘四不可盡’?勢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便宜不可占盡,聰明不可用盡。”這里的關鍵在于一個“盡”字。“盡”者,盡頭、絕頂、終點、極限之謂也;如果以花為喻,也就是“花意無余”“開到十分”。從辯證觀點看,事物達到頂點就要走向反面。老子有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祖輩傳留下來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惜衣有衣,惜食有食”之類的老話,則形象地闡明了因果關系。
《警世通言》中記載過這樣一個故事:唐代丞相王涯,官居一品,權壓百僚,僮仆千數,日食萬錢,享不盡榮華富貴。其府第廚房與一佛寺相鄰,每日廚房滌鍋凈碗之水傾倒溝中,穿寺流出。一天,寺中長老出行,見流水中有白物,近前一看,原是上白米飯。長老說聲“阿彌陀佛,罪過罪過”,便叫來伙工撈起溝內殘飯,用水洗凈,攤于篩內,曬干后用瓷缸收貯,兩年之內共積得六大缸有余。那王涯只道千年富貴,萬代奢華,誰知樂極生悲,觸犯了朝廷,待罪受審。其時賓客散盡,僮仆逃亡,倉廩盡為仇家所奪。家人二十三口,米糧盡絕,忍饑挨餓,啼哭之聲傳震鄰寺。長老聽到后,便將缸內所積米飯浸軟蒸后贈之。王涯吃后,甚以為美,遣婢女答謝。長老說:“這不是貧僧家常之飯,乃府上洗滌之余,誰知濟了尊府之急。”王涯聽罷嘆道:“我平日暴殄天物如此,安得不敗?今日之禍,必然不免。”當夜即服毒自殺。
三
看得出來,“好花看到半開時”,不到頂點,留有余地,并非僅僅限于審美,也不僅僅適用于日常待人處世,而是已經通過切身體驗,升華為一種生命智慧了。
晚清名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曾國藩,針對他的漢員大臣身份,在種族界隔至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危機深重,加之功高權重所帶來的險惡處境,有“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個字,以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之說。在這里,“惜福”與“保泰”相輔相成,互為表里。他在家書中說:“余蒙先人余蔭,忝居高位,與諸弟及子侄諄諄慎守者,但有二語,曰‘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而已。福不多享,故總以儉字為主,少用仆婢,少花銀錢,自然惜福矣”;“家門大盛,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之念,或可自保。否則顛蹶之速,有非意計所能及者”。為此,他勸誡諸弟:“當于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為衰時百事拂逆地步。”為了保全功名、地位,免遭朝廷疑忌,他毅然采取“斷臂全身”的策略,在剪除太平軍之后,主動奏請:將自己一手創辦并賴以起家的湘軍五萬名主力裁撤過半,并勸說其弟國荃借養病之名,請求開缺回籍,以避開因功遭忌的鋒芒。
如果說,曾氏的生命體驗表現為困蹙、被動與迫不得已,那么北宋理學家邵雍的妙悟,則是詩意的、優游的、主動的。且看他的七律《安樂窩中吟》的后四句:“美酒飲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開時。這般意思難名狀,只恐人間都未知。”為什么“都未知”?領略個中情境,有賴于凈而靜的心境。而世人追名逐利,奔走營求,整天處于遑遽、浮躁之中,又何談心境的凈、靜!可見,作為一種人生境界,這種感受是在閑適境遇中悟出的。
至于曾國藩所激賞的“花未全開月未圓”這句詩,其意境、情境及其悟出的心境,大致與邵老夫子的詩意相同。它也是出自北宋的一位名家。那天,書法家、大學士蔡襄悠閑地來到供奉文殊菩薩的吉祥院賞花,心有所感,即景抒懷,隨手寫下了一首七絕:“花未全開月未圓,尋花待月思依然。明知花月無情物,若是多情更可憐。”這個“可憐”,作可愛解;有些闡釋文章說成是可悲、可憫,謬矣。“憐”有多義,悲、憫之外,還有喜、愛、惜等多解。白居易詩句:“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可憐春淺游人少,好傍池邊下馬行”。前者“可憐”義為可愛,后者當作可喜解。(作者:王充閭)
 |
 |
責任編輯:康金山 |
- 2017-06-16龍海市開啟旅游文化周 倡導文明旅游
- 2017-06-16龍巖市委文明辦和新羅區文明委聯合舉辦“家和萬事興”好家風好家訓巡回宣講活動
- 2017-06-16洛江區召開全國文明城市總評迎檢動員會
- 2017-06-16善待城市修補匠也是一種文明
- 2017-06-16為共享經濟筑好文明籬笆
- 2017-06-16直播禮讓斑馬線傳文明新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