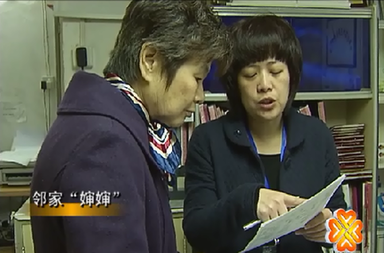夏衍與田漢、王瑩等合影。
偷渡離港
在離港前,廖承志找到當(dāng)時(shí)在八路軍駐港辦事處機(jī)要部門(mén)任職的潘柱,囑咐他:現(xiàn)在還有一大批文化人沒(méi)有離開(kāi)香港,有鄒韜奮、茅盾、張友漁、夏衍、胡繩等等,還有何香凝老太太、柳亞子他們,你一定要設(shè)法盡快找到他們,只要找到一兩個(gè),就能找到一大批,然后將他們安全送到九龍。九龍那邊我會(huì)布置人接應(yīng)你。他把身上僅有的幾百港元掏了出來(lái),給潘柱作為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
潘柱后來(lái)回憶,當(dāng)時(shí)他只有22歲,廖承志之所以把這么艱巨的任務(wù)交給自己,是因?yàn)樗皬男≡谙愀坶L(zhǎng)大,熟悉香港的道路。”
但是這種“經(jīng)驗(yàn)”也無(wú)法讓他“大海撈針”。接到任務(wù)后,潘柱“吃不下飯,睡不著覺(jué)”,一天,他突然靈光一現(xiàn),“只要找到在《華商報(bào)》工作的張友漁或生活書(shū)店的徐伯昕,不就可以打聽(tīng)到別人的行蹤了么?”
楊奇從事了幾十年的新聞工作,對(duì)于文化人的聯(lián)系方式比較熟悉,他告訴記者,“潘柱首先想到這兩個(gè)人,在當(dāng)時(shí)看來(lái),是順理成章的。在香港這么多文化人,總會(huì)形成自己的圈子,而報(bào)紙和書(shū)店正是文化人密集活動(dòng)的地方。”
張友漁回憶,潘柱找到他,是在他的房子旁“守株待兔”等了兩天。本來(lái),潘柱是想讓他提供些線索后,安排他先走,但他自愿留了下來(lái),幫潘柱聯(lián)絡(luò)。
當(dāng)時(shí)的文化人都已經(jīng)數(shù)易其居,雖然張友漁和他們素有交往,也很難聯(lián)系上。他后來(lái)還記得,找胡繩時(shí),好不容易打聽(tīng)到了地址,敲了半天門(mén),出來(lái)開(kāi)門(mén)的卻是個(gè)不相識(shí)的女人,說(shuō)了聲“沒(méi)這個(gè)人”就把門(mén)“啪”地關(guān)上了,他悻然走到了樓底,剛要離開(kāi),忽然,背后有人叫他。回頭一看,正是胡繩。
當(dāng)時(shí)文化人的小心謹(jǐn)慎,可見(jiàn)一斑。
胡繩帶著他,在胡同里碰到了戈寶權(quán),戈寶權(quán)提供了地址,他們找到了茅盾和葉以群,又在跑馬地找到了于毅夫,在銅鑼燈籠街找到了鄒韜奮……文化人像珍珠一樣層層串聯(lián),網(wǎng)絡(luò)逐漸擴(kuò)大,他們被分批安置到了多個(gè)臨時(shí)聯(lián)絡(luò)點(diǎn)中。
其實(shí),從周恩來(lái)到廖承志,都沒(méi)有給出一個(gè)足夠詳細(xì)的文化人營(yíng)救名單,最終獲救的800多人,是在潘柱等人的尋找中,基于平時(shí)社會(huì)關(guān)系動(dòng)態(tài)形成的,其中有從事文字工作的如茅盾、鄒韜奮,有活躍在影視界的如蔡楚生、司徒慧敏,也有何香凝、柳亞子這樣的抗日民主人士。
潘柱負(fù)責(zé)的文化人大部分都是要從陸上路線離開(kāi)的,這段行程的第一步,就是從香港偷渡到九龍。
茅盾是第一批走出香港的文化人,他曾經(jīng)寫(xiě)了一本名為《脫險(xiǎn)雜記》的回憶錄,詳細(xì)記述了他們夫婦二人從香港偷渡到九龍的親身經(jīng)歷:“(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上午,和我們住在一起的Y君(葉以群)從街上回來(lái),悄悄地告訴我們,明天可以過(guò)九龍去了。行李不能多帶……當(dāng)然也得改換服裝,于是都買(mǎi)了一套黑布的短衫(香港人稱(chēng)之為唐裝的)……”
之所以要做這樣的“改頭換面”,是為了能夠混入被疏散的難民隊(duì)伍中。
1942年1月9日清晨,包括茅盾夫婦、鄒韜奮在內(nèi)的9名文化人由交通員們沿途保護(hù),從臨時(shí)的聯(lián)絡(luò)點(diǎn)啟程了,交通員帶著他們繞開(kāi)大街,專(zhuān)走小巷。黃昏時(shí)刻,到達(dá)銅鑼灣的糖街。
埠頭上的船已經(jīng)停得密密匝匝。茅盾等人“通過(guò)一條大船,到了另一條大船上”,經(jīng)過(guò)漫長(zhǎng)的等待,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剎那”,船上的文化人才接到通知,“從大船走上了一條小艇,待到艙內(nèi)滿(mǎn)員了,艇就悄悄移動(dòng)了。”
此時(shí),正是夜間三點(diǎn)鐘——護(hù)送人潘柱親身試驗(yàn)過(guò),日軍每天都在這個(gè)時(shí)間進(jìn)行陸上換崗,海防也開(kāi)始松懈。
天公作美,這天正有大霧。濃霧籠罩在海面上,茅盾“從(小艇)竹篷的縫里向外窺望,遠(yuǎn)處有一座黑蒙蒙的東西,一閃一閃發(fā)著亮光。這大概是一條日本軍艦,那閃光是艦上打信號(hào)。”
但是這艘平日里會(huì)讓他們心驚膽戰(zhàn)的日本軍艦在此時(shí)已經(jīng)構(gòu)不成威脅了,次日清晨,天邊露出魚(yú)肚白的時(shí)候,小艇上的文化人“漸漸看得見(jiàn)陸地了,然而不見(jiàn)高大建筑”——這片陸地,就是九龍地界。
走陸路的文化人從九龍出發(fā),經(jīng)過(guò)元朗、大帽山,進(jìn)入了白石龍地區(qū),這里是當(dāng)時(shí)游擊區(qū)司令部所在地。
白石龍里茅寮客
經(jīng)過(guò)幾十里路的行走,通過(guò)元朗星星點(diǎn)點(diǎn)的日軍崗哨,翻越土匪盤(pán)踞的大帽山,一行人登上了一條名為“梅林坳”的山坳,在廖沫沙的記憶里,他們這批文化人到達(dá)這里時(shí),已經(jīng)是當(dāng)天的黃昏時(shí)分。在山坡下,可以看到有一個(gè)荒村,這里人煙不算太少,房屋被破壞的痕跡隨處可見(jiàn)。
今天的 “文化名人大營(yíng)救紀(jì)念館”南面,一片土地被圍了起來(lái),地面上,依稀可以看到幾許殘磚破瓦,在這塊空地旁,是一間面積不足30平方米的小白房。
黎金良介紹,這片空地上原本的建筑是白石龍村一座被廢棄的天主教堂,旁邊的小白房原來(lái)是教堂的修女房,數(shù)批文化人到了白石龍后的第一夜都是在這間房子里度過(guò)的。
但是就在文化人從這里撤離后不久,國(guó)民黨部隊(duì)來(lái)此侵?jǐn)_,一把火過(guò)后,教堂主建筑蕩然無(wú)存,修女房也塌了半邊,現(xiàn)在所看到的小白房已經(jīng)是紀(jì)念館建館后修復(fù)的成果。
雖然白石龍當(dāng)時(shí)屬于游擊區(qū),但10公里外就是日軍警戒線。當(dāng)時(shí)全村人口不足200人,幾批文化人先后到達(dá),如果住在村子里,很有可能暴露。
所以,第二夜,他們就走進(jìn)了深山之中。
楊奇當(dāng)時(shí)也在白石龍,他護(hù)送過(guò)一部分文化人進(jìn)“深坑”。“深坑”是白石龍附近陽(yáng)臺(tái)山和寶安龍華圩之間的一個(gè)山窩,易守難攻,比較容易隱蔽。他告訴記者,組織上說(shuō),這是一個(gè)“死任務(wù)”,讓他一定保護(hù)好這些文化人。轉(zhuǎn)移是秘密的,直到晚上7點(diǎn),天開(kāi)始黑了,他們才出發(fā),當(dāng)時(shí)他帶的那隊(duì)文化人大約有20人,包括茅盾、鄒韜奮、戈寶權(quán)等人。這些文化人都來(lái)自城里,基本沒(méi)在晚上走過(guò)山路,游擊隊(duì)員給每個(gè)人提前發(fā)了一根竹棍,讓他們借力。鄒韜奮因?yàn)檠劬Σ缓茫叩玫沧玻裢赓M(fèi)勁。
今天的紀(jì)念館里,文化人當(dāng)年的“住宅”被還原了:把松樹(shù)作為圍墻的柱子,屋頂搭草棚,里面架上橫桿,鋪上竹子,形成了一張長(zhǎng)兩米的“竹床”。這樣的簡(jiǎn)易建筑,被當(dāng)?shù)厝朔Q(chēng)為“茅寮”。
無(wú)炊無(wú)具,做飯是個(gè)問(wèn)題。
黎金良告訴記者,當(dāng)時(shí)不允許自己生火做飯的,因?yàn)橐坏┯袩熁鸷圹E,附近的敵人便很容易發(fā)覺(jué),就無(wú)法達(dá)到隱蔽的目的。紀(jì)念館中,至今保留著兩個(gè)銹跡斑斑的鐵桶和一根竹制的扁擔(dān)。——當(dāng)年,白石龍的村民就是利用這樣簡(jiǎn)陋的器具,在家做好飯菜后、送到山里。
在楊奇的記憶中,當(dāng)時(shí)游擊隊(duì)的條件非常艱苦,因?yàn)闁|江地區(qū)有日軍“掃蕩”,又有國(guó)民黨軍隊(duì)出沒(méi),地方亂,商人少,稅收也少。戰(zhàn)士們每天伙食供應(yīng)標(biāo)準(zhǔn)僅有生油五錢(qián)、菜金一角,但是給文化人的待遇翻了一番——生油一兩、菜金兩角。
只要條件允許,游擊隊(duì)都堅(jiān)持為文化人創(chuàng)造更好的物質(zhì)條件,戈寶權(quán)曾經(jīng)回憶“盡管游擊隊(duì)的條件很困難,我們每天還可以吃到粗糙的白米飯,干炸小魚(yú)或者蝦醬之類(lèi)的東西。部隊(duì)也很關(guān)心我們,還常把煮好的‘番薯泡糖水’(紅糖煮的番薯湯),用水桶挑來(lái)送給我們吃。有時(shí)還燒好熱水,要我們到部隊(duì)旁的樹(shù)林和河邊去洗澡。”
而文化人們也習(xí)慣用樂(lè)觀的態(tài)度來(lái)面對(duì)艱苦的生活,茅寮中的竹子床凹凸不平,很難入睡,茅盾卻說(shuō)“這是臥薪嘗膽,對(duì)付日本侵略者,應(yīng)該有這種革命精神。”
在深坑茅寮中的日子持續(xù)了十來(lái)天,文化人就被分批護(hù)送,前往東江的政治、經(jīng)濟(jì)中心惠州,但是此時(shí)的惠州,并不是一座對(duì)他們足夠友好的城市。
 |
 |
責(zé)任編輯:李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