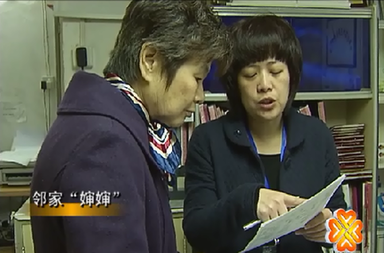“自述悔過書”寫好后,黃金榮又親自送到外灘中央銀行大樓軍管會處,由軍管會首長粟裕和副市長盛丕華接見訓話。據陪同黃去的陳翊庭回憶說,他們退出下樓后,陳忽發現攜帶的用物遺忘在樓上,于是叫黃在門口等待,他匆匆上樓去取。及陳再次下樓時,黃已不在,各處遍找無著。原來,黃恐生變故,急不可待的獨自一人回去了。
在悔過書中,黃金榮簡述自己的生平,歷數自己的歷史罪行,自稱要“自首坦白”、“立功贖罪”、“重新做人”云云,最后還說:“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為年紀大了(今年84歲),有許多事,已經記憶不清,話也許說得不適當,但是我的懊悔慚愧與感激的心,是真誠的!是絕不虛偽的!”
但查諸原件,黃的悔過書卻有兩份,且都有他的親筆簽名,一份與公開發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則出入較大,多有隱惡揚美,文過飾非之處,但對了解黃的某些歷史經歷也有參考價值,不妨簡單地介紹一下。
黃在這份從未公開披露過的悔過書中,自稱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支持者,說:“孫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護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時候,我保護送他上車,臨走的時候,中山先生對我說,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護,所以后來我認得了許多革命分子,像胡漢民與汪精衛他們就在革命軍打制造局的時候認識的。”又把自己說成是一個“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來上海的時候,難民很多,米糧恐慌,虞洽卿辦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為救濟、籌款”。到了“孤島”淪陷時,他也沒有落水做漢奸,說:“日本人時常來與我商量,要我出來做事,我總說年紀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絕他們。”總之,盡量為自己涂脂抹粉,然亦無可厚非。
另一方面,黃金榮又處處諉過他人,推卸自己的歷史罪責,說:“到抗戰勝利后,我也沒有做過什么事情,但是聽說我的門生,仍借我的名義,在外面招搖,干不好的事,因為年紀很大,也顧不了這許多。不過這種事情,是怪我過去太賣情面,收了好多門主,現在想想這種不好的情形實在錯誤。”
悔過書公開見報后,遠在香港的杜月笙異常敏感。他不知道這位老兄弟會說些什么,于是叫萬墨林快去找來當地報紙,他要仔細看一看。
這時,杜月笙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他半躺在床上,接過報紙,便看見萬墨林已經用紅筆鉤出了標題:“黃金榮自白書”,剛想接下去看,胸中卻感到有些悶氣,臉色立時顯得蒼白。萬墨林見狀,馬上接過報紙讀了一遍。
杜月笙微閉雙眼,仔細聽著,但未發一言。少頃,他睜開眼睛,說:“依再讀一遍。”
萬墨林坐在床邊,又從頭讀起,當讀至1927年四一二這一段時,杜月笙仿佛非常緊張,叫“停”了幾次,叫萬墨林慢慢讀。聽罷,杜如釋重負,長長地舒了口氣,說:“我懂了,我懂了。”
原來,黃金榮寫的這份自白書,述及四一二這一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將鎮壓工人運動的總頭子蔣介石及虞洽卿、張嘯林等人都點了名,獨獨沒有提到當時最“風光”的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這決不是黃金榮故意隱瞞事實,為他兩肋插刀,這個老于世故的把兄賣他還來不及呢!無疑,其中必定另有蹊蹺,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共在發出某種信息,既往不咎,歡迎他回大陸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杜月笙是何等樣人,自然心中有數,所以才會發出“我懂了,我懂了!”的獨白。
自此以后,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變化,至少一再拒絕了蔣介石邀他去臺,而時時萌動回大陸的念頭。黃金榮即使死了,也是死在上海,死在故鄉,葉落歸根啊。
黃金榮的自白書,竟然會對杜月笙起到這么一個作用,恐怕是黃本人始料不及的吧。事實恐怕也是如此,黃金榮第一份自白書交上去后,竟未獲通過,修改數遍,直到軍管會點頭,才重新謄抄了一份,就是公開見報的那一份。
而那時,潘漢年等人對杜月笙的統戰工作,正緊鑼密鼓,黃金榮的自白書無疑是重要一環。
但在上海,黃金榮的日子很不好過,至少他自己感到生命正在逐漸枯萎。
悔過書公開登報后,廣大市民不僅不予認同,反而更加激憤。黃金榮驚恐萬分,閉門不出,整日里提心吊膽,只好抱著“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念頭,坐在家里準備束手待“斃”。身體狀況也愈加差勁,坐在太師椅里,臃腫的身子幾乎站不起來,站起來也挪不開步子。加上媳婦李志清卷款逃往香港后,家中的開銷都成了問題,驚怕之外,加上氣急,使他本已衰弱不堪的身體和精神防線受到沉重打擊。這樣拖了近兩年,他終于一病不起,再也沒有爬起來。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黃金榮進入彌留狀態,由附近的永川醫院派一名護士前來,給他注射強心針,但亦無效,于當天上午停止了呼吸,終年86歲。
據當地公安分局在黃死后報告:“查黃金榮現年86歲,上海著名的大流氓,收有門徒萬眾,本區大世界、共舞臺、榮金大戲院皆是他的產業,當他于20日死時,大世界經理杭石君即報告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并申請更換大世界負責人姓名,以后便由黃金榮的得意門徒陳福康為主辦理喪事,計有馬筱峰、陳榮富、陳昌良(榮金大戲院經理)、沈茂貞、湯融、嚴興林、毛政紀、顧德昌、錢福林、陸正崇、朱文偉、陳益亭、王世昌、莊海寧、杭石君、陳榮炳等17人前來銷聲匿跡地看不出動靜地治喪。尸體于22日移往麗園殯儀館入殮,當晚在鈞培里一號黃金榮住宅中,備有九桌酒席,治喪過程中除上述得意門徒17人前來外,別無其他動靜。”
黃金榮死的那天,有人在復興公園后門的一塊黑板上,寫了“黃金榮倒了”五個大字,令人尋味。
杜月笙魂斷香港
杜月笙杜月笙,改名鏞,以號行。上海浦東人,1887年生。1903年在上海水果行當學徒,1911年參加八股黨,成為上海灘三大亨之一。后任上海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稅華人會監察。1927年組織中華共進會,配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1934年后歷任上海市地方協會會長、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等。抗戰爆發后,曾協助軍統從事情報、策反、暗殺活動。抗戰勝利后,曾任上海市參議會議長。
1949年4月27日夜晚,上海解放前夕,黯然神傷的杜月笙包了一艘荷蘭輪船“寶樹云”號,攜妻妾、子女、朋友、隨從數十人,逃離上海,到香港避風。
杜月笙到香港后,租住堅尼地臺18號底層,這是由他的一個門生替他租下的,僅三房一廳,比起上海華格臬路杜公館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他整日蝸居于此,幾乎是足不出戶。
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病復發,大概是一路勞頓,受了風寒,加之心情不好所致。一代大亨的最后歲月,基本上是在床笫之間度過的,有時甚至靠吸氧氣維持,到了后來,神經衰弱癥、心臟病和下肢偏癱接踵而至。
有人勸杜月笙找名醫來診治,他會幽幽地說:“老實講,若我今日仍在上海,不會如此的。”
經濟上,杜月笙也極為拮據,因為在香港不比上海,他賴以發跡的、上上下下的社會基礎一旦失去,就無從呼風喚雨了。他來港前,將上海東湖路附近的一幢洋房賣給美國人,得45萬美金,在香港就是靠這筆錢開銷。但杜府上下人口眾多,花費很大,每月總在6萬左右,畢竟是大亨,人來客去場面還是要應付得過去。
在香港杜府,整日價忙忙碌碌侍候杜月笙的,是姚玉蘭和孟小冬兩位。姚是杜的四太太,名伶孟小冬此時尚無名分,只是與他同居有年,她隨杜月笙坐船來香港后,始終體貼入微地照料他,給了杜月笙莫大安慰。
杜月笙與姚玉蘭
孟小冬原是在上海唱紅的京劇名角,人長得很漂亮,年輕時在北京曾一度跟隨過梅蘭芳。后來潛心向余叔巖學戲,得其真傳,并世無第二人,被譽為“冬皇妙音”。
孟小冬與杜月笙同居之后,再未登臺。到香港后,為給杜月笙解悶,小冬常教杜月笙學戲,杜也以此為樂。不久以后,杜月笙與孟小冬正式結婚。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體略有好轉,甚至還扔掉了輪椅、拐杖和氧氣瓶。逢天氣晴朗之際,還常在家人陪伴下出外散步。一次,路過錢新之家門口,還登門拜訪了他,并共進午餐,使這位老友不勝詫異。
 |
 |
責任編輯:李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