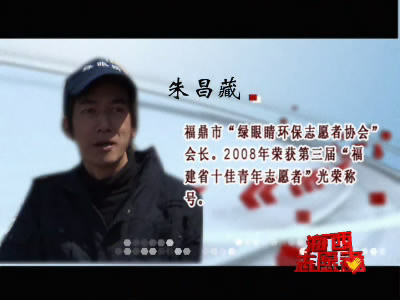酒桌即中國
酒精不燃燒,不算搞社交。
喝酒可大俗可大雅,可論國是可談風月,可攀交情可見性情,可怡情可亂性,可養生可傷身,可豪飲可小酌,只是不可無酒。
無酒不成席。酒是催化劑,桌是能量源。酒桌不是PK臺,是PR場。
在中國,酒是文化、禮儀、歷史、風俗;最后酒酒歸一,酒是關系,酒桌即中國。
情在口中,話在杯中,各地酒桌不同酒風。《新周刊》遍約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東北和香港的資深酒徒,談不同城市里的酒桌、不同酒桌上的人情世故、不同人情世故里的中國社會酒規則。
公款吃喝9000億,是國防開支的5倍、醫療投入的4倍,這叫“酒桌經濟”。拋開利益局,純扯淡、純聊天,開懷暢飲、放浪形骸,這叫“酒肉朋友”。“酒桌經濟”難免,“酒肉朋友”難得。更多的是我請你喝酒、你幫我辦事,喝酒成為一種工具理性。
今天,你喝了嗎?
必須買醉的中國人
中國朝酒晚舞
酒是“前啜”,桌是“后啜”。酒和桌構成中國人精神與話語交流的陣地,也是面臨各種社會壓力的逃避之所。
文/胡赳赳
王朔在《新狂人日記》中描述過一個叫“三哥”的,大家每天都頂著“三哥”的名目吃飯:周一,三哥要去天津了;周二,三哥又不走了;周三,三哥真走了;周四,三哥回來了。王朔說:“剩下的就全周末——必須的。”
這個三哥是典型的飯局達人,最“駭人”的一次是在某次聚會上,7個人互相介紹后發現,彼此全叫“三哥”,這幾率真是小之又小,愣讓王朔給碰上了。
吃飯其實很累,但再累也得吃。所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革命了,不就剩下“請客吃飯”么。美食專欄作家沈宏非說:“一周一個飯局是正常人,一天一個飯局是大紅人,一天三個飯局是交際花,一天很多飯局,是餐廳服務員。”
經濟學家茅于軾長期以來有個觀點,中國的糧食最起碼夠全中國再吃20年,所以他贊同退耕建房,這樣房價就下來了。中國人的現狀說到底是“吃穿住行”只解決了吃穿,沒解決住行。基本溫飽、略微小康、雖有中產、塔頂特權是社會的寫照。住,房價太高,行,交通太堵。吃和穿則蔚為大觀,鈔票化做飯票、布票仍是主旋律,于是往死里吃、往出格中穿。
 |
責任編輯:葉玲 |